第六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作品
台灣: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(2015年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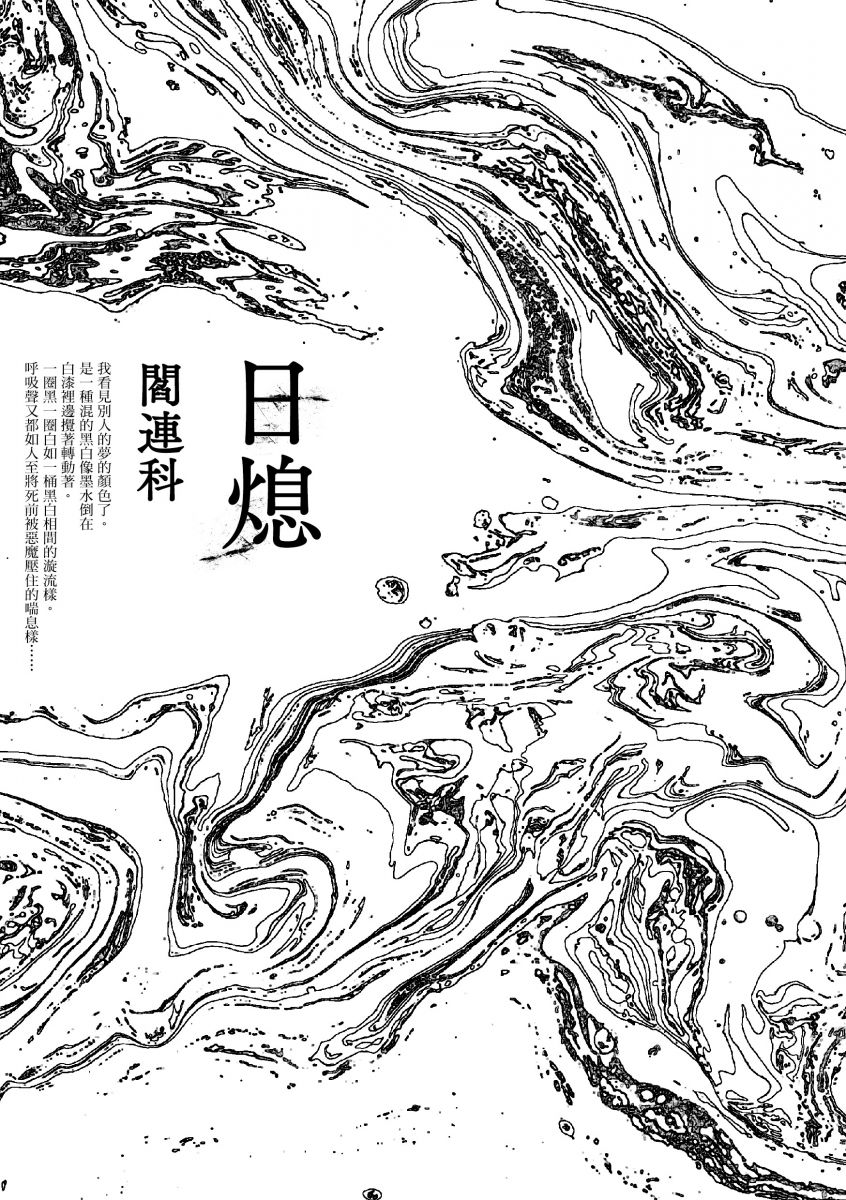 |
首獎作品評介
酷熱的八月天,麥收季節,一夜之間,夢遊症如瘟疫般蔓延於伏牛山脈的皋田小鎮內外。原本平常日光中隱伏的慾望,在鬼影憧憧的人群中爆發為荒誕不經的復仇、搶掠和「李闖式起義」,——以及匪夷所思的自我救贖。以中原大地的「死亡儀式」(葬喪傳統及其「變革」)為發端,小說展示了道德秩序和價值的大面積崩壞,一直擴展到「日頭死掉,時間死掉」的末日奇觀。永遠的黑夜意味著夢遊瘟疫的永無休止,意味著末日救贖的無望。小說藉由敘事結構的安排,對歷史時間的扭曲和現實的變形,把小說提升到超越語言的層面。無言之隱,泣血之痛,連文本中的那位作家「閻伯」也只能希冀自己可在夢遊中與之相逢。 閻連科以一個十四歲的鄉鎮少年作為視角和敘述者,發明了一種如泣如歌的具有音樂節奏的敘述語言,以繁密豐富的比喻重複地「叨叨」著,向失去了靈感的作家,向虛空,向高天諸神呼號,言說這不可言說的、似醒非醒似夢非夢的「世界黑夜」。閻連科堅韌而又充滿爆發力的文本實驗,再次給華文世界的文學讀者,帶來令人顫慄的閱讀驚喜。 作為「命定感受黑暗的人」,凝視時代的黑暗的光束,閻連科蘸著時代的黑暗書寫了一部堪稱當代經典的華文傑作。
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
黃子平教授 |
|
作者簡介
閻連科,1958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省嵩縣,1978年應徵入伍,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、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。1979年開始寫作,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堅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為人民服務》、《丁莊夢》、《風雅頌》、《四書》、《炸裂志》、《日熄》等十餘部;中、短篇小說集《年月日》、《黃金洞》、《耙耬天歌》、《朝著東南走》等十五部,散文、言論集十二部;另有《閻連科文集》十七卷。是中國最有影響也最受爭議的作家。曾先後獲第一、第二屆魯迅文學獎,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馬來西亞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獎;2012年入圍法國費米那文學獎和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。2014年獲捷克卡夫卡文學獎。2015年《受活》獲日本「推特」文學獎,2016年再次入圍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,同年《日熄》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。其作品有日、韓、越、法、英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以色列、荷蘭、挪威、瑞典、捷克、塞爾維亞等二十多種譯本,已在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外文作品七十多本。2004年退出軍界,現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,為教授、作家和香港科技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客座講授。
|
 |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閻連科於頒獎典禮上發表之得獎感言全文
因為卑微,所以寫作——「紅樓夢獎」授獎演講辭
女士們、先生們、同學們及尊敬的評委:
在這個莊重的場合、莊重的授獎活動中,請允許我首先說一個真實的故事:不久之前,我在香港的科技大學以教書的名譽,有了一段海邊的天堂生活。五月的一天,夜裏熟睡至早上五點多鐘,正在美夢中沉浸安閒時,床頭的手機響了。這一響,我愈是不接,它愈是響得連續而急湊。最後熬持不過,只好厭煩地起身,拿起手機一看,是我姐姐從內地——我的河南老家打來的。問有甚麼事情?姐姐說,母親昨天夜裏做了一個夢,夢見你因為寫作犯了很大的錯誤,受了嚴重處分後,你害怕蹲監,就跪在地上求人磕頭,結果額門上磕得鮮血淋漓,差一點昏死過去。所以,母親一定讓姐姐天不亮就給我打個電話,問一個究竟明白。
最後,姐姐在電話上問我,你沒事情吧?
我說沒事,很好呀。
姐姐說,真的沒事?
我說,真的沒事,哪兒都好。
末了,姐姐掛了電話。而我,從這一刻起,想起了作家、文學和寫作的卑微。——從此,「卑微」這兩個字,就刀刻在了我腦絡的深皺間,一天一天,分分秒秒,只要想到文學,它就浮現出來,不僅不肯消失,而且是愈發的鮮明和尖銳,一如釘在磚牆上的鐵釘,紅磚已經腐爛,鏽釘卻還鮮明的突出在那面磚牆上。直到七月中旬,我因訪從美國回到北京,時差每天都如腦子裏倒轉的風輪,接着,又得到《日熄》獲得「紅樓夢獎」的消息,於是,就在不息的失眠中,不息地追問一個問題:曹雪芹為甚麼要用畢生的精力,竭盡自己的靈魂之墨,來寫這部曠世奇書《紅樓夢》?真的是如他所說,是因為「一技無成,半生潦倒」,才要 「編訴一集,悅世之目、破人之愁」嗎?如果是,在他這種「悅世之目、破人之愁」的寫作態度中,就不僅絲毫沒有文學的卑微,而且,還有着足夠的信心,去相信文學的尊嚴和它的堅硬與崇高。
可是,今天的作家,除了我們任何人的天賦才情,都無法與曹雪芹相提並論外,誰還有對文學的力量、尊嚴懷着堅硬的信任?誰還敢、還能說自己的寫作,是為了「悅世之目、破人之愁」?當文學面對現實,作家面對權力和人性極度的複雜時,有幾人能不感到文學與作家的虛無與卑微?作家與文學,在今天的中國,真是低到了塵埃裏去,可還又覺得高了出來,絆了社會和別人前行的腳步。
今天,我們在這兒談論某一種文學,談論這種文學的可能,換一個場域,會被更多的人視為是蟻蟲崇拜飛蛾所向望的光;是《動物莊園》裏的牲靈們,對未來的憂傷和憧憬。而且,今天文學的理想、夢想、崇高及對人的認識——愛、自由、價值、情感、人性和靈魂的追求等,在現實中是和所有的金錢、利益、國家、主義、權力混為一談、不能分開的。也不允許分開的。這樣,就有一種作家與文學,在今天現實中的存在,顯得特別的不合時宜,如野草與城市的中央公園,荊棵與都市的肺部森林,卑微到荒野與遠郊,人們也還覺得它佔有了現實或大地的位置。當下,中國的文學——無論是真的能夠走出去,作為世界文學的組成,還是雷聲之下,大地乾薄,僅僅只能是作為亞洲文學的一個部分,文學中的不少作家,都在這種部分和組成中,無力而卑微地寫作,如同盛世中那些「打醬油的人」,走在盛大集會的邊道上。於國家,它只是巨大花園中的幾株野草;於藝術,也只是個人的一種生存與呼吸。確實而言,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現實,還需要不需要我們所謂的文學,不知道文學創造在現實中還有多少意義,如同一個人活着,總是必須面對某種有力而必然的死亡。存在、無意義,出版的失敗和寫作的惘然,加之龐大的市場與媒體的操弄及權令、權規的限制,這就構成了一個作家在現實中寫作的巨大的卑微。然而,因為卑微,卻還要寫作;因為卑微,才還要寫作;因為卑微,卻只能寫作。於是,又形成了一個被人們忽略、忽視的迴圈悖論:作家因為卑微而寫作,因為寫作而卑微;愈寫作,愈卑微;愈卑微,愈寫作。這就如堂吉訶德面對西班牙大地上的風車樣,似乎風車是為堂吉訶德而生,堂吉訶德是為風車而來。可是意義呢?這種風車與堂吉訶德共生共存的意義在哪兒?!
難道,真的是無意義就是意義嗎?
記得十餘年前在長篇小說《丁莊夢》和《風雅頌》的寫作之初,面對現實與世界,我是經過自覺並自我而嚴格的一審再審,一查再查,可今天回頭來看這些作品的寫作與出版,到底還有多少藝術的蘊含呢?
《四書》、《炸裂志》、《日熄》,這一系列的寫作與出版,閱讀與批評,爭論與禁止,其實正構成了作家與現實如堂吉訶德與風車樣無休止的對峙、妥協;再對峙、再妥協;再妥協,再對峙的寫作關係。可到事情的尾末,不是風車戰勝了堂吉訶德,而是堂吉訶德戰勝不了自己的生命。戰勝不了藝術與時間的殘酷。是作家自己,懷疑自己文學中藝術量存在的多寡與強弱。事情正是如此,風,可以無休止地吹;風車,可以無盡止地轉,而堂吉訶德,終於在時間中耗盡了生命的氣力,交械給了風車和土地。生命在時間面前,就像落葉在秋風和寒冬之中;而藝術,在時間和大地面前,就像一個人面對墳墓的美麗。如此,在這兒,在世界各地,我總是面對某種文學的藝術,默默含笑,誠實而敦厚地說:現在,中國好得多了。真的好得多了。若為三十多年前,你為文學、為藝術,寫了「不該寫」的東西,可能會蹲監、殺頭,妻離子散,家破人亡。而今天,我不是還很好的站在這兒嗎?不是還可以領獎、遊覽和與你們一塊說笑、吃飯並談論文學與藝術嗎?
請不要說我這是一種阿Q精神,甚至也不要說是堂吉訶德的收穫。我清晰的明白,這是一種寫作對一種卑微的認識,對卑微的認同。更重要的,是我和我的文學,對卑微的認領——自我而主動的認領!希望通過自我、自覺的認領,可以對卑微有些微的拯救,並希望通過被拯救的卑微,來拯救自己的寫作;支撐自己的寫作。在這兒,卑微不僅是一種存在和力量,還是一種作家與文學存在的本身。因為卑微而寫作,為着卑微而寫作;愈寫作愈卑微,愈卑微愈寫作。事情就是這樣——文學為卑微而存在,卑微為文學的藝術而等待。而我,是卑微主動而自覺的認領者。卑微,今後將是我文學的一切,也是我生活的一切。關於我和我所有的文學,都將緣於卑微而生,緣於卑微而在。沒有卑微,就沒有我們(我)的文學。沒有卑微,就沒有那個叫閻連科的人。卑微在他,不僅是一種生命,還是一種文學的永恆;是他人生中生命、文學與藝術的一切。
在《一千零一夜》中那則着名的「神馬」的故事裏,神馬本來是一架非常普通的木製馬匹,可在那人造木馬的耳後,有一顆小小的木釘,只要將那顆木釘輕輕按下,那木馬就會飛向天空,飛到遠方;飛到任何的地方。現在,我想我的卑微,就是那顆小小的木釘;我的文學,可能就是能夠帶我飛向天空和任何一個地方的木馬。當我沒有卑微的存在,當我的卑微也一併被人剝奪,那麼,那個木馬就真的死了,真的哪也不能去了。所以,我常常感謝卑微。感謝卑微的存在;感謝卑微使我不斷地寫作。並感謝因為寫作,而更加養大的那個作家內心那巨大的卑微。這個卑微,在這兒超越了生活、寫作、出版、閱讀,尤其遠遠超過了我們說的現實與世界、權令和權規的限制及作家的生存,而成為一個人生命的本身;成為一個作家與寫作的本身。它與生俱來,也必將與我終生同在。也因此,它使我從那飛翔的神馬,想到了神馬可至的另外一個遙遠國度的宮殿。
有一天,皇帝帶着一位詩人(作家)去參觀那座迷宮般的宮殿。面對那結構複雜、巍峨壯觀的宮殿,詩人沉吟片刻,吟出了一首短詩。在這首短極的詩裏,包含了宮殿的全部結構、建築、擺設和一切的花草樹木。於是,皇帝大喝一聲:「詩人,你搶走了我的宮殿!」又於是,劊子手手起刀落,結果了這個詩人的性命。就在這則《皇宮的寓言》裏,詩人或作家的生命消失了。 可是,這是一則悲劇嗎?不是。絕然不是!這是一齣悲壯的頌歌。歌頌了詩人的才華、詩人的力量和詩人如同宮殿般壯美的天賦。而我們呢?不要說一首短詩,就是一首長詩,一部長篇,一部浩瀚的巨制,又怎能包含整個宮殿或現實世界中哪怕部分的瓦礫和花草呢?
我們的死,不死於一首詩包含了全部的宮殿,而死於一百首詩,都不包含宮殿的片瓦寸草。一百部長篇也難有多少現實的豐富、扭曲、複雜和前所未有的深刻與荒誕。這就是我們的卑微。是卑微的結果,是卑微的所獲。所以,我們為卑微而活着,因為卑微而寫作,也必將因為卑微而死亡。而今,「紅樓夢獎」授於《日熄》這部小說,我想,也正緣於評委們看到了一個或一代、幾代卑微的作家與寫作的存在,看到了作家們卑微的掙扎和卑微因為卑微而可能的縮命般的死亡。因此,尊敬的評委們,也才要把「紅樓夢獎」授於用卑微之筆寫就的《日熄》,授於認領了卑微的我,要給卑微以安撫,給卑微以力量,以求卑微可以以生命的名譽,生存下來,使其既能立行於宮殿,又能自由含笑地走出宮殿的大門;讓詩人既可在宮殿之內,也可在宮殿之外;可在邊界之內,也可在邊界之外;從而使他(她)的寫作,盡可能地超越現實,超越國度,超越所有的界限,回歸到人與文學的生命、人性和靈魂之根本,使詩人及他的卑微可以繼續的活着並吟唱;使作家相信,卑微既是一種生存、生命和實在,可也還是一種理想、力量和藝術的永遠;是藝術永久的未來。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偉大與永恆。使作家相信卑微的生命和力量,甘願卑微,承受卑微,持久乃至永遠地因為卑微而寫作,為着卑微而寫作。
2016年9月22日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決審委員評語節錄
《日熄》是一本象徵意義深刻的小說。在本質上,它挖掘人性,也諷刺現實。小說的結構完整而嚴謹。描寫一個村鎮裏有些人患了夢遊症,他們把壓抑在潛意識的慾望和暴力都以行動發洩出來,連沒有患夢遊症的人也乘機姦殺擄掠,後來亂子擴大到整個地區,出現了集體夢遊症。夢遊症一波一波地擴散,寫得井然有序。在時間處理更是精準而有創意。故事的時間由第一天下午五時寫到第二天早上九點半,在時空方面加了魔幻的成分。早上六點是整個地區最混亂的時刻,時間從六點就不前行了,直到有人壯烈犠牲,霾霧才散開,人才清醒,時間才運行。 《日熄》不只寫人性的黑暗面,也寫光明面,小說的敍述者念念是個十四歲的孩子,有一點痴呆,他的小名念念影射《四十二章經》的「念念為善」。念念和他的父母代表社會的良心和正義。家人試圖阻止眾人夢遊。念念的父親李天保曾為生活而傷害過人,懷著還債的心態,以非常怪誕的方式,把自己化為火球,創造了人為的日出,讓時間恢復運行,人間恢復秩序。《日熄》在對人性深刻的描寫上,在對心理層次的處理上,在善與惡的對峙上,寫得驚心動魄,是一部富魔幻色彩的、意義深刻的小說。
第六屆「紅樓夢獎」決審主席
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院長
鍾玲教授
閻連科的《日熄》讓人想起了卡繆的《鼠疫》,小說以象徵的手法,寫了一個鎮上人們一夜之間集體患了夢遊症,他們在夢遊裡互相廝殺、搶劫,陷入犯罪的恐怖之中,究其原因,是因為太陽遭到了遮蔽,陷入日蝕狀態的黑暗之中,人們在昏睡不醒中喪失了理性,演繹出種種非理性的可怕行為。
但也有人(如李天保)在夢遊中把內心深處的懺悔說了出來,並且一家一戶地上門道歉,取得人們的諒解;更有甚者,當他意識到日熄的危險之後,毅然發動昏睡中的村民,以利作誘,指揮村民把大量的屍油推到山頂,用自焚點燃了油,燃起熊熊大火,取代日頭,終以喚醒夢游中的村民,迎來了新的一天。
這是一個集體的噩夢書寫;這是一個人性的壯烈之歌。在對人性中自私貪婪等醜惡因素的批判的基礎上,揭示出人是世界上自我拯救的第一要素。可以說,這是一本中國版的《鼠疫》,卻比《鼠疫》更加悲壯、強烈,對人性也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。
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
陳思和教授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