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作品
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(2011年)
台灣: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(2008年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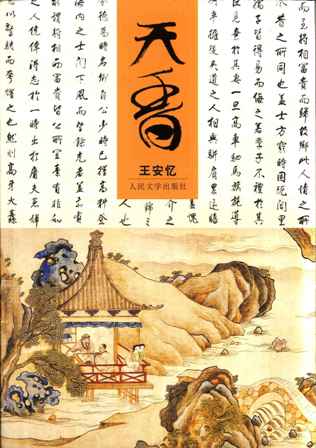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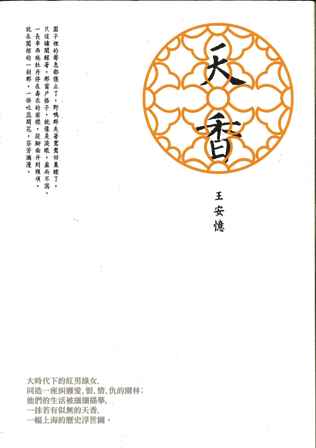 |
首獎作品評介 王安憶的《天香》寫明朝中期至末期,上海申姓士大夫大家族四代人的故事。申氏家族的園林「天香園」為江南的名園,而家族女眷的刺繡「天香園繡」竟成為「天下第一繡」。這部小說氣勢恢宏,幾十位家族人物的塑造,皆有特色。歷史人物如徐光啟的穿插,也自然地融入,並且能整體地、渾然呈現精緻而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。主要呈現了兩種中國的生活藝術傳統,即園林文化與女紅文化,並且帶出多種次文化傳統,如製墨、傳統樂器演奏、製果醬等等,無不描繪細緻。就情節的發展而言,申家的園林文化由興寫到衰,而申家的女紅文化則方興未艾。整體而言,這部小說表現了女權主義思想,申家的男性大多為個性比較軟弱的世家公子,而女眷中如小綢、沈希昭、申蕙蘭皆個性堅強果斷,才華卓越,終能以她們聞名天下的刺繡,在經濟上,名譽上,撐起沒落的家族。她們的刺繡結合了女紅技巧與士大夫的繪畫傳統,故能獨步稱絕。她們之間的姊妹情誼堅固,甚至超越生死。小說中並提升傳統的工藝師的地位。故事把社會的邊緣人物,以及受壓抑的女性,移至中心的主體位置。《天香》的語言採用了古雅的書面語,卻非常清暢自然。此小說可說是江南文化的百科全書,女紅文化的經典,生動表現四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志趣節操之傳世鉅作。 第四屆「紅樓夢獎」決審委員會主席 鍾玲教授 |
|
作者簡介 王安憶,1954年出生於江蘇南京,1969年初中畢業後,曾赴安徽插隊,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、中國作家協會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。作品有長篇小說、中短篇小說、散文及兒童文學作品,包括《紀實與虛構》、《長恨歌》、《憂傷的年代》、《處女蛋》、《隱居的時代》、《獨語》、《妹頭》、《富萍》、《香港情與愛》、《剃度》、《我讀我看》、《現代生活》、《逐鹿中街》、《兒女英雄傳》、《叔叔的故事》、《遍地梟雄》、《上種紅菱下種藕》、《小說家的讀書密碼》、《啟蒙時代》、《月色撩人》等等,其許多作品被譯成英、德、荷、法、捷、日、韓、以色列等多種文字。曾獲全國優秀中篇、短篇小說獎,長篇小說《長恨歌》更獲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、第五屆茅盾文學獎,以及第一屆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。長篇小說《啟蒙時代》更獲第二屆「紅樓夢獎」決審團獎。 |
 |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王安憶於頒獎典禮上發表之得獎感言全文
今年七月,去溫州,沿楠溪江而至岩頭古村。古村的歷史可追溯到初唐,明嘉靖年間可稱全盛,最為瞻目的建設是一套完整的水利循環系統。從北邊高地接源楠溪江,向南邊低地貫通,中間以涵洞與水碓分流,三池五湖蓄水,供灌溉和生活,注流六公里河道及二十畝水面,最終再入楠溪江。大功告成於嘉靖三十五年,正是在《天香》開篇時候的三年前。倘若我之前到過這個地方,那麼天香園裡就可能會有獨立的水系,蓮池的供水與出水都會複雜和精緻,要有水碓、涵洞、溪流,景致當豐富一籌。更要緊的是,建園子的大師傅要多一位,何方人氏,姓甚名誰,哪樣的相貌脾性,又會引出多少造化人工的高論!說起來是遺憾,其實是機緣不夠,造一個園子,哪怕在紙上,也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,諸項成因。即需要耐心等待條件成熟,且又不能錯過心動一刻,這就像開花時節,錯過了就不再來了。我們所做的,其實相當盲目,準備了的不定能用著,頂用的又恰恰沒有準備。古語裡說的「有意栽花花不發,無心插柳柳成蔭」,什麼是「花」,什麼又是「柳」,「有意」與「無心」之間,有沒有關聯呢?就是說多少次「有意」才能促成一次「無心」?或者無論多少次「有意」也未必能夠邂逅一回「無心」。
在上海最早的城區南市,遺留著一些舊地名,比如露香園路、青蓮街、萬竹街、九畝地……從這些地名綽約可見當年園子的規制以及變遷,那露香園就是我的天香園的摹本,要重建一個幾百年前的園子,無論文史知識還是想像力,都是挑戰,這些舊地名無疑為天香園制定了方位以及內容。我沒有考證癖,也不具備復原歷史的野心,只是一種寫作的笨拙,事物如若缺乏具體性質,我就無法構築小說世界。我的人物必得在一個具象的環境中才可活動起來,演繹他們的命運,可是,對於那個年代,我沒有一點感性的認識,偏又不巧,我要寫的故事就發生在那個年代。市政建設改變了城市的地貌,那些舊街道已經消失,連南市這個行政區域也從上海重新編制中合併取締,露香園上不知道覆蓋上多少考古層,我的天香園究竟在哪裡生根,才能開出花來呢?
2008年底,我一邊排列年表,一邊勾畫地圖。年表從嘉靖三十八年開始,從各路正野紀表得來的零星片段,依序寫下;地圖是在南市老城廂地圖基礎上,新舊地名參照。然後將我的人物嵌入其中,為他們制定前生今世。當人物來到這已然消失的時間和空間裡,模糊的景物漸漸變得清晰起來,就好像被激活了似的。所以,事情有時候是反著來的,我原先以為環境必須是肯定的,人物才可生活其中,不期然間,人物卻驅散環境的模糊氤氳,使之水落石出。這就是想像的傳奇性,可能是此決定彼,也可能彼決定此,還可能是共生共長。究竟是何種情形,大約就要回溯寫作的初衷了。
事情要從上海的風物「顧繡」說起,在這現代城市淺近的歷史上,「顧繡」幾可稱上古跡了,在地方誌和掌故上留下隻言片語,說是顧氏女眷善繡,家道中落之後,且以女紅維持生計,並設帳傳授,藝滿天下。等到我們生活的時代,當年盛景殆盡無餘,連傳說都已風過耳。歷史但凡到上海,節奏立即加速,時間疊加著過去,許多東西都留在了褶縫裡,不知什麼時候遺漏出來一點,這就是機緣的意思了。多少年裡,有時候會想一想,舊式的大家裡,女眷供養族人,還是以閨中針黹,覺得很有幾分意趣。即便到了近代,「五四」以後的新女性,講的是獨立,度量和能量也未必有此境界。《傷逝》裡的子君,要依憑涓生得衣食;《傾城之戀》的白流蘇,爭取是在婚娶,好依憑范柳原得衣食;《寒夜》裡的樹生,有供養汪文宣的意志,可到底拗不過時局,最後落敗;上海名伶阮玲玉,經濟自立還有餘裕,結果是男人劫色又劫財,香魂隕落……顧氏女眷究竟是何等人物?她們所供養的又是什麼樣的男人?那個家族又有著什麼樣的秉性?似乎,幾下裡都氣定神閑,並沒有經歷革命的激烈和動盪。每一回想起,那一幅畫面便會生動幾許,疑惑也增添幾重,問題接踵而至,越來越呈密集之狀,就有一種催迫加緊,再也等不得了。這些人,已經在等待我了,等在某一個未可知的地方,所以,說是歷史,其實更是未來,是將來未來之時,對於存在的現在時來說,都是渺茫和虛空。
然而小說是這樣一種仿真的東西,沒有具體性,就無依無憑。所以,還是要回到史實裡去。史料,上海的史料,都不那麼靠實,更接近坊間閒話,說道是,顧繡是顧家一名妾所帶來,名已遺失,只存姓,繆氏,於是就有了「閔女兒」;史料又說,「顧繡」的至高期在於「韓希孟」,至今收藏於故宮與上海博物館的繡品,多有韓希孟的款,這就是「沈希昭」的真身;史料還說,顧繡流傳世間是因「顧玉蘭」,她早年守寡,以設帳授教撫養婆母與幼子,「蕙蘭」就此出場。有了人,就有了前因後果,那「閔女兒」是如何進到申家——也就是顧家,以名諱之忌,改「顧」為「申」,並非有為上海立傳的野心,只是就便,上海的大戶就用上海的名,僅此而已——閔如何進來申家,境遇如何?正房妻室如何人品?就有小綢;天降大任於希昭,希昭又是如何來歷?就要細說從頭;蕙蘭是要設帳,當是在市井,接觸的人事必要繁雜許多,就有了戥子,李大,范小,北京人叫「胡同串子」,也就是小市民……就這麼一生二,二生三,不敢說三生萬物,總之越生越多。為人物寫結局其實是非常傷感的時刻,活潑潑的一個個離你而去,留下自己,真是寂寞得很。來時是晚明,去已是明亡,就又有一種蒼茫。誰讓都是明朝的人,明朝的事呢?所以,造一個嘉靖的園子也是事不得已。
寫作就像一個神遊,神遊回來,如夢初醒,情何以堪。能夠得到知音,得到褒獎,實是意外之喜,喜出望外,謝謝「紅樓夢長篇小說獎」的評委。而我決不會因這「紅樓夢」的獎名以為已經接近了《紅樓夢》,《紅樓夢》是一本天書,中國的小說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實現的神聖,寫作者們也因此有了小說的理想。
2012年8月28日 上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決審委員評語節錄
王安憶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壇最重要的作者之一。寫作三十餘年,某些作家可能擔心“如何超越他人”但王安憶唯一需要擔心的是“如何超越自己”,經過《紀實與虛構》,《長恨歌》,《富萍》,《遍地梟雄》,《逃之夭夭》,《上種紅菱下種藕》等優秀長篇作品之後,這的確是個難題。但憑著《天香》這樣的一部力作,王安憶不但超越了自己過往的寫作風格,也使得華語小說書寫達到新的高峰。通過大家族的興衰,顧綉這門手藝的細膩描繪,王安憶呈現“大上海”的前傳,而《天香》這樣的一本“大書”註定是二十一世紀華文小說的新經典。
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
白睿文教授 (Michael Berry)
這本書正如同一架巨幅的刺繡畫,一個獨立自足的宇宙 ,細微款款,佈局透過明朝上海灘園林的草創 、興旺 、而至蕭條。每一細節密密錯織:從明代中國的畫論 、書法、背後的宇宙觀、 藝術論 ;人面對生死無常的時間態度;一種"多寶閣"式的,將文明 、工藝 、器皿的講究 ;烹飪 、節氣 、 喪嫁禮儀……在這種封閉的 ,古典靜態世界裡,人際關係的不斷翻造 錯織,形成一不可思議的小說時空。
在一故事中人皆無意識 ,時代之巨變正已不可擋之勢,如遠方雷聲而來;將一種南方文人或貴族閨秀審美講究,過渡至自為 ,生機充滿的民間社會 。
以《長恨歌》為代表,王安憶應已是華文長篇小說家最重要指標之一。她寫女孩兒的細微心思、迂迴猜臆、一種女性壓抑的靜態憂鬱、過於敏感於是將內向維度無限綻放的小說視窗,本身已成為典律。然《天香》一書,卻硬生生從頭蓋起,完全和八零年代以降中國現代小說語言拉開距離;另闢一整套修辭,另一種攬鏡照相,另一座四百年前「上海」的「清明上河圖」。對百餘年來 , 遭遇「現代」 而離散崩解之華人心靈史,重描了一個明亮溫暖 、 豐饒典麗 的精神原鄉。
第三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《西夏旅館》作者
駱以軍先生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