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届「红楼梦奖」首奖作品
香港:天地图书﹙2012年﹚
台湾:大田出版﹙2012年﹚\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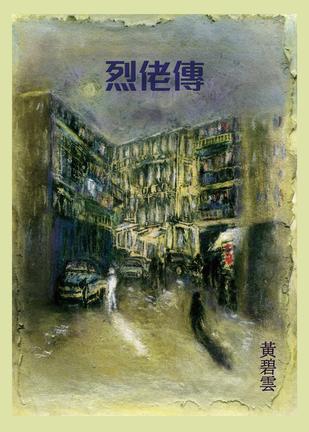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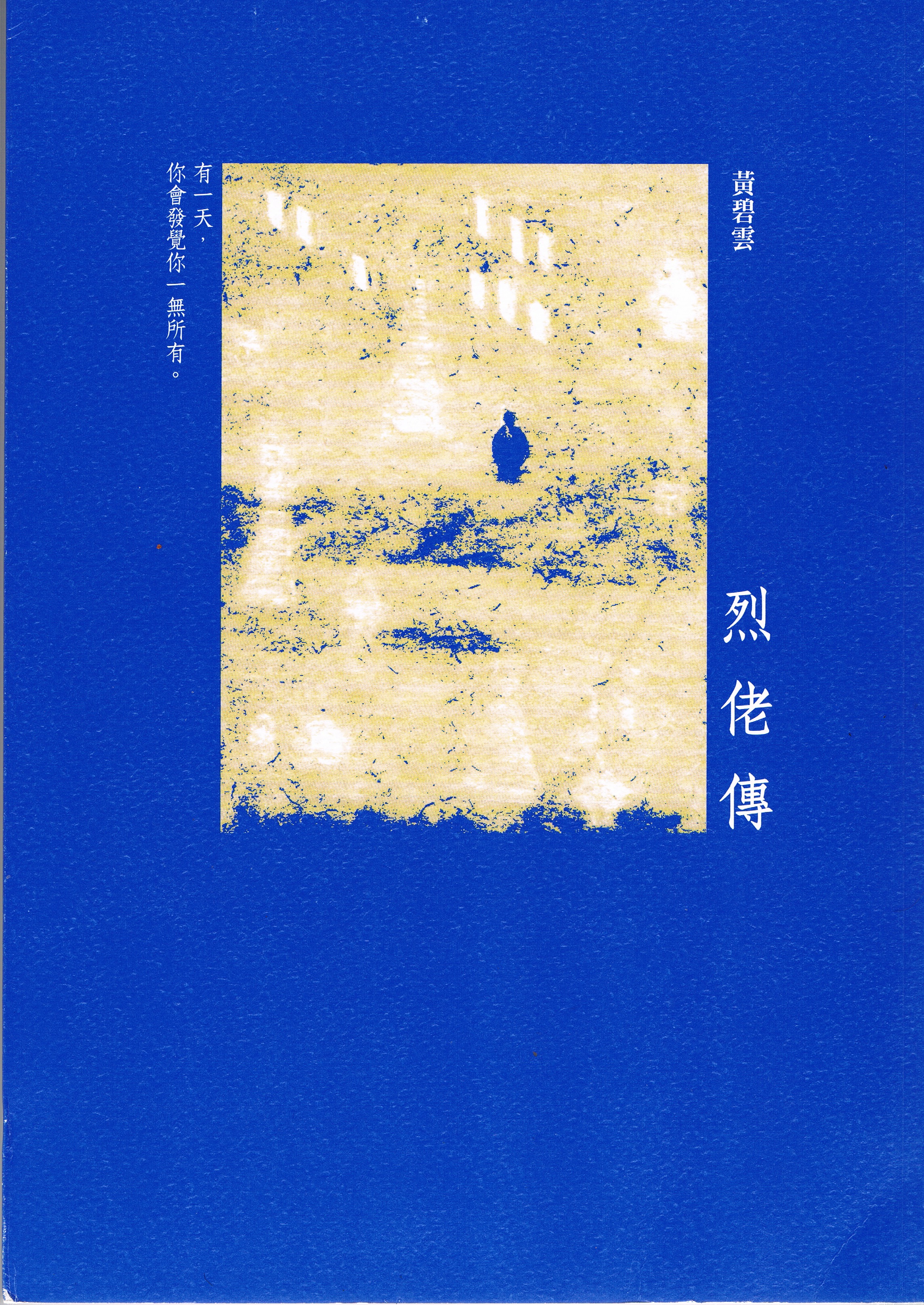 |
首奖作品评介
黄碧云《烈佬传》的题材是描绘香港最底层的、最边缘的一群人,包括吸毒的、黑道的、偷窃的、赌博的、半辈子在监狱蹲的那群人。由一九五零年代写到二十一世纪初。地点围绕在湾仔地区和各个监狱。主要人物「我」十一岁就离家出走,十三岁就加入帮派、还吸毒、赌博、贩毒、作扒手的少年。在那底层社会打滚一生。他是一个平凡人,但敢于接受命运。因为本性善良,常怀助人之心,到了六十岁终于戒毒成功,被朋友接受,融入社会正常的生活,并且担任社会工作的义工,帮助别人戒毒。他对命运的承受力,他的苦尽甘来,皆令人动容。黄碧云一反其以前作品中驰骋的想象语言和暴力美学,在此小说中呈现极其收敛、理性、简约的风格,以悲悯的心情呈现炼狱中的众生。
第五届「红楼梦奖」决审委会员主席
钟玲教授 |
|
作者简介
黄碧云,1961年生于香港。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犯罪学系犯罪学硕士,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律专业文凭。曾任新闻记者,为合格执业律师。曾获得第三届、第六届及第十二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、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奖、第六届香港书奖、《亚洲周刊》2012年度十大小说、黄碧云-《号外》「创想生活奖2012-文学」、第一届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新秀等等,并且多次入选台湾文学小说选集。
|
  ﹙作者自画像﹚ |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黄碧云于颁奖礼上发表之得奖感言全文
文学的权力与自由精灵的怀疑与否定 黄碧云
谢谢红楼梦奖评审很宽容的给《烈佬传》这样卑微的一本小书,这个重要的奖项。
或者因为在香港成长受教育,而且在香港生活的缘故,我从来不觉得文学是甚么一回事,不过小时喜欢读,有能力时便写。
我们从来不会以为自己有甚么影响力或权力,书卖得很少,读者很少,金钱的回报很微薄,也没有甚么社会地位。每次被问及职业,我都感到羞愧而不敢作答。后来索性答,无业。在香港写作,从来不是一个职业。
写作是娱乐吗?如果每天早上六时起来写,做一下别的事,又继续写,偶然出去一下,急忙回家,好像有婴孩等吃,不能不回;这种娱乐,恐怕很多人都吃不消。
写作是使命?我们都羞于承担。但觉得有必要一写,可能就是使命。
更确切的说,写作是呼唤,而且无可逃避,跑到甚么国家,躲在甚么房间,不写了不写了,突然有一句,坐下,便写。
写一二千字,扔掉,三四千字,让我再想想。
读书,去图书馆找数据,访问。回来想想,再写,这一次,四五万字,扔掉。去探访,做一下义工吧,为他们做点读书小组,小说写也好,不写也好。我没想过一定要写。
静下来,又写。这一次,写成一本书,但不觉得对,没有那种「就是这样的了」的感觉。放下,去一下甚么国家,做一下甚么别的事,继续去探访。我要了解人,了解他们的现实。我不觉得对,因为我没很了解。
又再试。第二稿,比较好,不够好。
《烈佬传》写了出来,我就将它忘记。作品对作者而言,生命只在房间。离开了作者的房间,对作者来说,作品已经完成,与我无关。
作品属于读者。《烈佬传》写得这样浅白的小书,它可以属于任何识字的人。可能不算是文学作品,我觉得很好。
文学是开放的,没有门槛,任何人都可以进来。我第一次去到巴黎,我很年轻,最令我惊异的事情,是在地车睡觉的流浪汉,躺着看沙特的一本小说。或者记在心,我会想,如果流浪汉都会看我的小说,就好了。
因为我当初写作,我想是因为反叛。我无法改变世界,我起码可以创造一个世界,而我在其中,成为自由精灵。
这种写作,不是高高在上,万人景仰的。我希望我的读者是失意的人,失败的人,有缺陷的人,而书本,给这些人安慰和力量。正如我在前人的书本,得到安慰与力量。去认清自己的缺陷。
文学它有粗野的生命力。八十年代我回到中国,青年写诗都是用手写油印,自己钉装,在朋友之间传阅。我回到香港,有人寄这些地下诗给我,我捧在手中,舍不得阅读。粗野文学,令人快乐。
因此我不认为,文学应该是艰深的,虽然我也写过难读的作品,那是我没有约束自己的缘故;连以难读见称的哲学家康德,都说「每一部哲学著作都该通俗流行、为大众接受;如果哪本哲学著作不是这样的话,那它就有可能是在貌似高深的辞令迷雾之下,隐藏了一派胡言。」较后的叔本华同样认为「没有甚么事情比写出无人能懂的东西更加容易,而以人人都可以明白的方式,表达出重要、深奥的思想则是最困难不过的。令人费解的文字是与无知和缺乏理性紧密相关的。」当然,小说比哲学宽容,因此艰深难懂的小说,未必不是文学作品。
作品离开房间,就是已出之物,也就是公物。它的命运,与作者的关连很少。一本被扔去回收,很多本转来转去,或有卖来卖去都卖不出,成为杀人凶手,砸死人。
有很少数的作品,被有权力编写文学史的人阅读,并且正名:这就是文学作品。幸好在正名之先,作品已经被好些不明所以,只因为喜欢的人阅读。
正名有它的机制:学校、评论、成名作家的喜好、奖项。虽然我认为,文学最忠诚可靠的辨识者,是时间,也就是,世世代代的读者。不是很多文学作品可以经得起世代的阅读。留下来的,是我们文明的宝藏。每次我读到喜欢的古典作品,总会惊叹:能写的,都写了。陈情记述的,能写得比《史记》?言辞绮丽,岂及《楚辞》?内心独白,能写得像莎士比亚那么尽?
正名甚至不是进入时间竞赛的入场券。我相信一百年之后,今日被称为文学作品的,仍然有读者的,非常少。但我们已经不在,因此不重要。
人有能力认识我们生活经验以外的事情,让我们谦逊,也不得不谦逊。
作品的生命,离开作者之后,依靠的是读者,包括有评论与话语权的读者。我想作品和人一样,都在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,正名让作品死亡的过程减慢,如果作品本身有这样的生命力,有机会生存下来,我不敢说成为经典,我从来没想过会成为经典。
正名机制,超越个别作品,让文学更新甚至重生,十九世纪法国俄国的写实主义小说,到二十世纪,为比较抽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所替代,拉丁美洲小说于下半世纪冒起,算是打破欧洲为中心的局面。我们要阅读并非自己生活范围接触到的作品,只能依赖正名机制。
即是说,正名机制拥有塑造历史素材的权力。作品原来只是可以给流浪汉阅读,忽然得势。
权力与自由,互相排斥。并不是说,拥有权力的人就有自由,相反,权力愈大,尤其是政治权力,个人所受到的限制与反击也愈大。我们都读过马奎斯写独裁者的寂寞,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个前港督,他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,因为他说,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,只好去行山。有权力的人,连讲一句真心相信的说话,都要思前想后。我从来不羡慕有权力的人的生活。
在香港,拥有经济权力的人,看来有较大的人身自由。怪不得很少人愿意从政。
文学权力,一旦拥有,会否伤害自由精灵?
一个重要的奖项,评论,读者喜好,原来会将作者,这自由自在,无人理会的写作人,变成作家,会影响他人,并且在社会有发言权的人。这一点我拒绝去承认,因此不大有意识。
但我会写。写作本身,到今时今日,仍然非常纯粹,不受任何权力或写作之外的考虑诱惑。精灵只在自由的空间才会呈现浮游。
精灵来到这自由的边界,会稍一停留,问,这是你吗?你会不会迷失?你要走得多远?你可以对抗整个世界吗?
只要我写,读者会累积,即使我不接受奖项,我仍然无法逃避我拥有的权力:作品为人阅读,我作为个人的言行,会影响他人,或好或坏。
无法逃避的事情,面对它。
奖项是荣耀,奖项将作品正名为文学,给予作者个人权力,成为作家,这荣耀也是责任。得到这个奖项,我听到一些对我个人的批评;对作品的批评,很正常,作品能引起讨论,我觉得是作品的光荣,但个人受到月旦,我觉得因为这个荣耀,令到他人对我的道德期望更高。
作者可以飘忽不定,作家却要言行一致。并且当人心混乱的时候,作时代的良知。
我大概已经到了负责任的年纪。并且因此而意识:有重量的自由。自由精灵,轻省飘浮,不停留,责任有根,将个人扎定于地。这亦体现了,自由的道德制约。
张力来自相反方向的努力:升高,着地;飘浮,确定。写作的时候,我仍然是那个自由精灵,但面对社会的时候,我必须是一个以良知行事的公民,谨言慎行。正如我较早前所说,奖项效应很快便过去,奖金我会用来做下一本书的资料搜集的旅费,也会用光,但我感谢这个奖项,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限制与责任,我战战兢兢,但也斗志高昂,向着我下一作品,向着我人生的其他困难,行使自由意志,也承担责任,无畏前行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决审委员评语节录
《烈佬传》以一个古惑仔的自述,将一群「黑暗的孩子」生存的空间,转化为边缘人物毒海生涯的时间和命运,乃将都市的(湾仔)地方志转换为小说,香港六十年沧桑变迁的许多历史大事件毫不起眼地隐伏其中,小说遂也为「飘摇之岛」的「此处」描图立传了。「烈」是黄碧云的生命哲学或历史哲学。「以轻取难,以微容大,至烈而无烈」,烈佬们的「烈」,不在帮派江湖的暴力摧残,也不在法律机器的规训教化,而在他们以一己必坏之肉身,面对命运时的坦然夷然。黄碧云舍弃自己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学风格,坚决删略抒情和主观形容词,将情节简化到只剩下日常对话和动作。这部小说的匠心独运,是将粤语口语精心提炼为平实、结实、表现力内敛的文学语言,从叙述层面赋予「不识字的口述者」以主体身分和尊严。《烈佬传》是黄碧云继《烈女图》之后更上层楼的又一杰构,是对世界华文小说的一大贡献。
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教授
黄子平教授
严格遵守虚构的纪律,在自定的形式里极尽想象,那就是自述者的角度来实现叙事人的认识——一个无自觉性的生命如何向茫然虚空中汲取存在的理由,而逐步被时间和社会驯服,走入规范,以此,展现文明对荒蛮的收伏,修剪去旁枝错节,厘清混沌,宏大主流,那些细碎的个体的性质,亦湮灭其中,成为历史的沉渣。黄碧云只能在纸上留下印记,纪念它们曾经的生动,冷暖自知,在正史之外开辟另一章,这不就是小说家的妄念吗?
第四届「红楼梦奖」首奖《天香》作者
王安忆教授



